读书·抄书·买书·著书——我与书的缘分
崔山佳
我的学历很低:初中毕业务农,其间做过泥工、木工等,后担任浙江宁波奉化尚桥公社电影队放映员。1977年高考恢复招生,参加了大学考试,现记忆犹新:全公社74人参考初试,只3个初中生,我是其中之一;初试后,淘汰了36人,全是高中生;复试后,剩下9 人,初中生只我1人。后因各种原因,录取在宁波师范学校余姚分校(中师)。工作后参加电大学习(汉语言文学专业,专科,成人业余)、本科(汉语言文学专业,函授,浙江师范大学)。这样,我的正规学习时间是:小学五年半,初中两年(语文一年1本教材,只学过两篇古文,《三元里抗英》《愚公移山》),师范一年半(虽然是77级,但开学是1978年3月,1979年8月毕业),刚好九年,相当于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制的水平。
1993年评为中专讲师,1998年评为中专高级讲师(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分校第1个评上副高职称的教师),2004年调入浙江财经学院(现为浙江财经大学),2005年转评为副教授,2006年评为教授,是全校学历最低的教授之一。
现为浙江财经大学三级教授,硕士生导师。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兼职研究员(2020年11月至2025年10月)、中国语言学会会员、全国方言学会会员、中国训诂学会会员。研究方向为近代汉语、汉语方言、欧化语法现象等。《古汉语研究》《汉语学报》《汉语史学报》《汉语史研究集刊》《汉字汉语研究》《宁波大学学报》等语言学刊物或大学学报审稿专家。
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6项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,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晚明以来吴语白话文献语法研究及数据库建设”(21&ZD301)(首席专家)(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层次最高、资助力度最大、权威性最强的项目类别,代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国家水准,也是教育部学科评估和各类办学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)。在《中国语文》《语言学论丛》《中国语言学报》《古汉语研究》《方言》《语言研究》《明清小说研究》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《汉语学习》《修辞学习》《红楼梦学刊》《语文建设》《辞书研究》《语言研究集刊》(复旦大学)《汉语史研究集刊》(四川大学)《文献语言学》(北京语言大学)《燕赵学术》(河北师范大学)《中国方言学报》《语文建设通讯》(香港)《澳门语言学刊》(澳门)《现代中国语研究》(日本)《中国语学研究·开篇》(日本)《汉字研究》(韩国)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,出版专著9部(另有1部书稿即将完成)。
下面说说我与书的缘分。
一、读书
我是1964年上小学,文革时读三年级,没有《语文》教材,只有《毛主席语录》,白封面平装本,1角5分一本,后说是毛主席的书要免费。语文成绩就背语录,背出后在语录的左上角打一个五角星,期末看五角星多少计成绩。课外基本无书可看。幸亏家里有《毛泽东选集》与鲁迅的书,我都看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77年省考作文题目是《路》,因读过鲁迅的书,《故乡》中有这样的话:“希望本无所谓有,也无所谓无,这就像地上的路,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作文中我引用了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后听人说,引用鲁迅的话很有用,能打高分。
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知识青年丛书,其中有《中国近代史》,我有幸看过。1977年高考历史考试有一名词解释是“黑水党”。这道题目绝大多数考生未考出,一名高中毕业生考后问学校知识较渊博的老师,该老师也不知道,而我居然考出了该题。还有巧合的是,考地理的那天中午,等待考试时,几个熟悉的人在一起讨论地理会考哪些内容,有人说,京广线要经过哪些重要城市,哪些河流等,我带了一书包书,马上一起翻看地图。我又想,京沪线也很重要,查了一下地图,才发现江苏徐州这个城市地理位置很特别,像雄鹰的嘴一样,向西凸出。后试卷中竟有填写中国地图中的几个重要城市,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徐州等,杭州因有杭州湾,特征很明显,上海也一眼能识别,南京因在长江边也好辨析,如不在考前看过地图,无论如何是填不了徐州的。
考上师范后,我真的是“如饥似渴”“博览群书”。我本是电影放映员,视力很好,但读师范一学期后,眼睛就近视了,戴上了眼镜。学校规定,放假前要把所借的书还给图书馆,而我却每次借了一大包书范图书馆老师的厚爱!

崔山佳老师读过的书,上面是崔老师密密麻麻的批注
当然也看报纸和杂志。那时校学生阅览室看报纸、杂志人很多,我就跑到教师阅览室看。1978年12月,陶斯亮一篇长达万余字的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——给我的爸爸陶铸》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,引起轰动,卢新华创作的短篇小说《伤痕》1978年发表于《文汇报》,这两篇名作我都是在教师阅览室看的。那时,看的书很杂,古今中外,诸子百家,上至天文,下至地理。年轻人,看书杂一些也好,知识面广一些有好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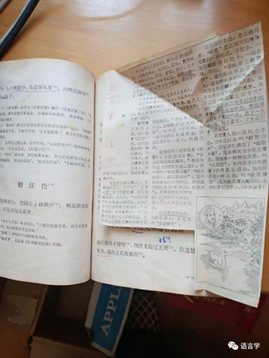
崔老师的剪报
后来,对我来说,直接的好处是,好多论文的选题就是在看书或报刊中得来的。一次在看金圣叹的《杜诗解》时,发现有“来岁如今归不归?”的诗句,马上联想起朱德熙先生的著名论文《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》(《中国语文》1985年第1期),论文中说杜甫诗歌中没有“VP不VP”句式。“说有易,说无难”,哪怕是著名语言学家都是如此。我写成不到300字的短文《杜甫诗中也有“VP不VP”句式》,投给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,短文居然发表了(1985年第6期),同时,我给朱德熙先生写了信,朱先生不久给我回信,表示感谢。吕叔湘先生有一短文《“生前”和“身后”》,引用辛弃疾《破阵子》“赢得生前身后名”后指出:“这‘生前’和‘身后’是固定的。只有‘生前’,没有‘身前’,只有‘身后’,没有‘生后’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”我在看《全唐诗》时,发现2个“身前”的例子,后来又发现其他朝代也有,有的是“身前身后”并列运用,写成《“身前”也有词例》,也投给《中国语文》,也发表了(1988年第4期,巧的是,已故的陇东学院刘瑞明教授也投稿给《中国语文》,发表时把我们两人的姓名并列在一起)。投稿的同时,我也给吕先生写信,吕先生因年事已高,回信是委托秘书写的。一般认为,“是”虽是动词,但却是“判断动词”,后面不能带“了”“着”“过”。后在看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时,发现有一句是“难道是了美国人”。“姓”是“关系动词”,一般也认为后面不能带“了”“着”“过”。其实,“姓+了”的例子更多。后来以《“姓了”与“是了”》为题发表在《中国语文》1991年第4期。在调入浙江财经大学前,在《中国语文》共发表12篇短文,《中国语文》是语言学的权威期刊,正因为有这12篇论文,才能从小县城调入杭州的大学。到目前为止,已在《中国语文》发表15篇长短不一的论文。
古人说,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我们不能这么功利,但多读书确实有很大好处。据媒体报道,现在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,这不是好现象、好风气,趁年轻,应该多多读书,多多读纸质的书。
二、抄书
文革结束,百废待兴,书店里的书少得可怜,而同学中有的从家里带来了一些好书,那时没有复印机,就只能抄,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,其中诗歌和散文抄得多。如抄过莎士比亚《雅典的泰门》中关于黄金的一段著名的话:“金子!黄黄的、发光的、宝贵的金子!……这东西,只这一点点儿,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,丑的变成美的,错的变成对的,卑贱变成尊贵,老人变成少年,懦夫变成勇士。”还抄过莎翁《哈姆莱特》中多段著名的独白。抄了好几本笔记本。记得刘半农有一篇《饿》的散文,真好,“饿”的心理活动写得很逼真,很感人,作为三年困难时期过来的我,深有体会。后来,我在奉化一中教初中时,把此文刻印给学生,并布置他们写《饱》的作文,有一位女同学写得很好,很细腻地写出了“饱”的感受。
三、买书
在做电影放映员时,我积累了一些“私房钱”,后全用于读师范时买书。当时,除向校图书馆借书外,还在梁弄镇的书店里买了不少书,与营业员认识后,只要书店到两本书,一本给师范图书馆,一本就留给我,真是“受宠若惊”。
工作后,虽工资很低,第一学期只有16元一月,后来是36元,每年总要省下一些钱买书。结婚生子后,这个爱好继续着。这方面要感谢我的爱人,虽偶尔也有一些埋怨,但大多情况下是默认的。到2002年时,老家奉化举行“十大藏书家”评选,我名列第2名,列第1名的是当时已70多的老教师。现在我的藏书更多了。退休后在奉化居住,去年年底乔迁新居,把旧房子的书全部搬过来了,还有一大半书在杭州的家里要运过来。
虽然校图书馆能借书,但搞学术研究,最好是自己有藏书,有的常要查,方便,更重要的是,可在书上作记号、写眉批等。我的一些论文的选题就是在这些记号、眉批中得来的。如《围城》中有一特殊的语法现象,虽只有5例,但却很珍贵,这都是在读书中积累下来的,如:
(1)辛楣俩假装和应酬的本领至此简直破产,竟没法表示感谢。(第148页)
(2)辛楣俩去了一个多钟点才回来。(第156页)
(3)鸿渐送她出去,经过陆子潇的房,房门半开,子潇坐在椅子里吸烟,瞧见鸿渐俩,忙站起来点头,又坐下去,宛如有弹簧收放着。(第219-220页)
(4)鸿渐俩从桂林回来了两天,就收到汪处厚的帖子。(第236页)
(5)到香港降落,辛楣在机场迎接,鸿渐俩的精力都吐完了,表示不出久别重逢的欢喜。(第288页)
后以《〈围城〉中有“人名+俩”的说法》为题发表在《中国语文》1993年第5期上。
2020年我在《中国语文》第1期上发表《南方方言“数词+亲属名词”类型考察》,字数14000多,参考文献50本/篇,主要是自己的藏书。第10部专著已完成书稿,参考文献多达1280余本/篇,也主要是自己的藏书。
四、著书
2004年生日那天,我正式办好了调入浙江财经大学的手续。调入本校后,我的学习、研究的平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学校有“中国知网”等可下载论文等,记得当时我在宁波电大看到该校老师可这样做,而我论文中的语料大多来自自己的藏书与所订的10多本语言学杂志,我是多么的“眼馋”啊!学校人文学院资料室有《古本小说集成》,我1992年去厦门时曾在书店中看到过,我印象当时要1万多或2万多,那是上世纪90年代,凭个人的力量根本买不起。有一次去宁波大学文学院找好友周志锋教授,看到院资料室就有这套书,我又是多么的羡慕。现在总算能一饱眼福了。后因各种原因,未很好地利用这套书,至今感到深深的遗憾!2004年调入本校后,我的第一本专著《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》就在当年9月由武汉崇文书局出版。2006年3月,我的第二本专著《近代汉语词汇论稿》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。至今已出版9本专著,另7本书如下:
3.《宁波方言词语考释》,巴蜀书社,2007年11月。
4.《现代汉语“潜显”现象研究》,巴蜀书社,2008年12月。
5.《近代汉语动词重叠专题研究》,巴蜀书社,2011年2月。
6.《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专题研究》,巴蜀书社,2013年6月。
7.《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》,语文出版社,2015年7月。
8.《吴语语法共时与历时研究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8年12月。
9.《汉语方言数词和量词特殊用法研究》,语文出版社,2022年1月。
第10部专著《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》已经完成书稿,将交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另外,手头还有2部书稿。
五、体会
1 尽信书,不如无书
可能与我主要是靠自学有关,我不迷信,到目前为止,我与赵元任、王力、吕叔湘、朱德熙、陆俭明、蒋绍愚、沈家煊、邢福义等一流语言学家的论文、专著商榷过。也与余光中先生的论文商榷过。
赵元任先生认为汉语无“坏吃”的说法,他的《汉语口语语法》(1968:344)指出,作副词用的“好-坏”和“容易-难”这两对反义词之间有一种参差现象:首先,能说“这菜好吃”(good to eat),不说“这菜坏吃”,得说“这菜难吃”;“好吃”还有“容易吃”的意思。“容易吃”只有一个意思,而“难吃”除了“不容易吃”的意思外还有“不好吃”(tastes bad)的意思。后来,沈家煊先生的《不对称和标记论》(2015:165)引用了此说法。其实,宁波方言口语中有“坏吃”,如“坏吃”(不好吃,难吃)、“坏吃果子”(“比喻不好对付的人”)、“坏吃芋艿(头)”(“比喻不好对付的人”),尤其是奉化话中的“坏吃”也有“比喻不好对付的人”之义。后来写成《宁波方言中的“坏X”说法》,参加第10届国际吴方言研讨会,论文入选论文集《吴语研究》第10辑。


钱钟书先生给崔山佳老师的信
《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专题研究》一书中,与王力先生等的好多看法有商榷。如人称代词带定语,学界现有5种说法:1.汉语固有说;2.欧化或日化说;3.外语影响说;4.修辞说;5.综合说。以前,“欧化或日化说”影响最大。我的第1部专著《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》(2004),《也谈“定语+人称代词”结构的来源》(《中国语文》2008年第4期),《“人称代词带定语”一定要用“的”字吗?》(《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2期),《现代汉语“潜显”现象研究》(2008),《〈关于“定语+人称代词”〉献疑》(《修辞学习》2009年第1期),《也说“定语+的+人称代词”结构的类型》(《语言与翻译》2011年第3期),《〈关于“定语+人称代词”结构的思考〉商榷三题》(《宁波大学学报》2012年第3期),《〈也说“人称代词受修饰”现象〉质疑》(《语言与翻译》2012年第2期),《〈略论人称代词带修饰语的形式〉质疑》(《中国语学研究·开篇》,2012年10月),《〈语体动因对句法的塑造〉补说三题》(《现代中国语研究》,2012年10月),《“定语+人称代词”宋代已经成熟》(《汉语史研究集刊》第20辑,2015 )都坚持“汉语固有说”,是该说的主要代表。
王力先生认为汉语没有概数用法“五七”,吕叔湘先生认为近代汉语使用不长时间就消失了。我通过多年考察后发现《红楼梦》后仍有很多例子,现代汉语、当代汉语仍有运用,而且一些方言、南方民族语言也有。后发表《关于“五七”、“三五七”概数用法的补说》(《古汉语研究》2015年第2期)。
吕叔湘先生有一短文《“把”字二题》(1984)举有一个特殊的例子——“能一气管两个不连在一起的宾语”的介词“把”字用法,例如:
(1)妈妈可惊了神,把地擦了又擦,桌子抹了又抹。
吕叔湘先生认为这个“把”字在很多地方超出了一般介词的用法。上句一般情况下应是这样表述的:
(2)妈妈可惊了神,把地擦了又擦,把桌子抹了又抹。
董秀芳教授的《现实化:动词重新分析为介词后句法特征的渐变》(2009:26)把这种用法称作介词“并列删除”现象。我的《现代汉语“潜显”现象研究》(2008)、《介词“把”等特殊用法历时考察》(2010)、《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》(2015)都有论述,古代汉语、近代汉语、现代汉语共计有26个介词有“并列删除”现象。曾记得《介词“把”等特殊用法历时考察》在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年会时,著名语言学家沈家煊先生在讨论时向我提出了问题,《中国语文》副主编方梅教授会后对我说,她对该文很感兴趣,后论文发表在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14期上。
关于“V在了N”(如“放在了地上”)也有争论,朱德熙先生否认双音节动词不能进入此格式,邢福义先生认为此式能成立,但认为是新兴语法现象。我经过考察发现明末已有例子,清代更多,现当代作家中,老舍的例子有几百例,解放后也一直在运用,改革开放后,使用频率更高,且有发展。《“V在了N”等格式历时考察》(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15期,2012年7月)、《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》(2015)都有论述。最近在看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中,发现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单音节动词135例,双音节动词49例,从两者的比例看,双音节动词似乎是作家中用得最多的之一。同时,后面的“N”(名词性成分)也有新的发展,如:由实到虚、由空间到时间、表示年龄、表示数量等。该文将参加第二十二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,已收到通知。


北京大学朱德熙先生给崔山佳老师的信
2 找准自己的定位
不同的人,因性格等众多原因,适合不同的研究对象。我大叔叔是浙江省著名诗人,出版了10多本诗集。我年轻时也曾写过诗,寄给他修改,没有成功。后来我才感觉到,我的形象思维能力欠缺,而逻辑思维能力较强,而搞语言,尤其是搞语法研究,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。如汉语言文学专业,是搞文学还是语言研究,语言研究,是搞语音、文字、词汇,还是语法、语用,都与某人的性格等有关。
3 天生我材必有用
像我这样,全日制学习只有9年的人,也能作出一些成绩,现在人们的学历大大提高了,条件也好多了,如搞学术研究,现在有网络,数据库等,查阅资料太方便了。想当初我在看24册的《全唐诗》过程中,只发现2例“身前”与“身后”搭配的例子,当时真是如获珍宝。那时我要花费多少时间,而现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就能解决。
我坚信:天生我材必有用!
4 活到老,爱书到老
2017年我退休后,仍然爱书,仍然坚持不懈地搞科研。2018年成功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,2018年、2020年2次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论文,2021年,我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,这意味着我将继续买书、读书、著书……